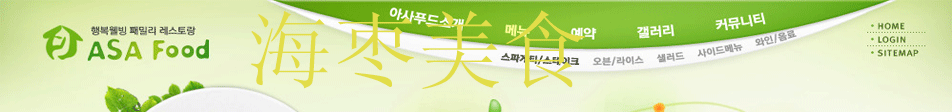|
编者按 边疆是大国治理的关键,形象模糊却令人遐想无限。《法律和社会科学》曾经在年推出“法律的边疆”专题。时至今日,边疆问题仍未过时。 语言是现代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其中有何深意?如何看待诉讼法中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 原标题《这里没有普通话:藏区的双语司法实践》,载《法律和社会科学》年第期。作者孙少石,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文章推送时有删减。 这里没有普通话:藏区的双语司法实践 文 孙少石 一这里没有普通话今天主流的关于法律和语言关系的讨论,几乎集中在法律诠释、诉讼语言、谈判技巧这些烙有欧陆法学传统的领域。但这些理论存在一个未曾言明的假定,即语言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大致统一、初步格式化了。而把这个假定再向前推一步,则意味着一个物质的、历史的前提,如同欧陆国家一般,国家面积较小,多平原地形,民族单一。在这样的环境中语言统一相对容易,语言差异甚至不为人所察觉。有了这些条件的支撑,法律诠释学才不是无本之木,也因此可以看到这一知识的地方性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确实已经使相当数量的城市呈现出这一理论适用的背景。但中国毕竟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中国正在并仍旧需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渐进地完成建构,因此尤其不可对中国基层、西部与边疆治理掉以轻心。尽管当地面貌大有改观,但伴随中国总体发展的推进,过去没有遇到、无法预料的深层次问题也渐次暴露出来。 图:年,在悉尼声援祖国、反对分裂的留学生、华侨 举例而言,当一个法官在藏区解决纠纷时,发现当事人与他不仅语言不通,连文字也不通,怎么办?找翻译。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呢?或者翻译专业本领不过关,甚至歪曲原意,从中作梗呢?如何质证,如何询问、讯问,如何审判,又如何抗辩,审判结果听不懂、判决书读不懂,接下去如何执行?如果长期不能克服语言不通的难题,谈什么法律向边疆的扎根,法律背后的国家又将何去何从?本文正是受这些连珠炮式问题的激发,切入到法律与语言的关系,更确切地讲,讨论的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为了建立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法律在不同语言与文化共同体之间是如何穿行的。 其实两年前,我模糊地感到语言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它同时也应当成为一个大国语境下政治学和法学有必要关切的问题,比方说,日语,我是听不懂的,是一门外语,闽南语对我而言,同样听不懂,它是一门“外语”吗?不是。那什么是“外语”?外国人使用的语言。什么是外国人?什么又是“国”?闽南语、日语与我都是有距离的,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因为语言迥异而将操持着闽南语的福建人看作反正同样也沟通不了的日本人或是其他外国人?仅仅因为有能够交流的普通话?但我也懂得英语,怎么没有产生对英语世界的国家、民族认同? 因此这不纯粹是个说话、识字意义上的语言问题,而需要认识到语言是不同时空中的人们在生命、情感、认同上建立起的某种神秘联系的具体附着,所以仅仅有语言是不够的。但反过来,没有语言却也万万不行,想一想没有普通话,中国各地顽守本土方言,这必定大大提高人员、信息跨地区的费用进而最终限制自由、频繁地流动,一个生动活泼的全国性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得起来,统一的法治就只是一句空话。语言之于政法不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制度,而是一个支持、推动操作性制度的基础性制度。 作为促成目标的努力之一,我现在继续分享当时的核心主张,即驱除现代西方法学理论中将语言统一视作当然或普世的假定,在历时性研究中把握中国将原本裂碎化的方言统一为不与任何单一地方存在代表性关联的官方标准语言—普通话—所发挥的不可估量的宪制与司法功能。但需要修正或补充的是,当时的我还是把问题考虑的简略化了,在揭示问题之时落入了一种视角上的遮蔽。这样的理解是基本成立的,但直到转向边疆法治,直到独自进入藏区试图与普通藏民对话,直到触碰到另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格局和组织形态,我才猛然醒悟也许是那时难以避免的疏漏:藏区不仅没有不动产,这里也没有普通话。 在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访谈时,几位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藏区政法部门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双语人才的匮乏,一些偏远的基层法院已经濒临人才断层。据他们说阿坝县法院招录了专职翻译,因此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受到了上级法院的重视。在这一提醒下,我决心去一趟阿坝县,四川省的西北角,去看看语言在藏区是如何与法律勾连并成为一个问题的。 年8月我在阿坝县法院只遇到一位翻译J,另一人D在外地参加司法考试培训。这位我见了面的翻译,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藏人,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研修的是数学和法学双学位,后来回到阿坝在藏文中学当老师,01年11月进人县法院,专职翻译工作,不仅承担了法庭上向当事人的口头翻译,而且据他讲法院所有文书都得由他们进行双语翻译。他坦率地告诉我,这样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希望法院至少再多招一个人,然而1月初我再和他联系时,尽管又增添了两名翻译,但令他沮丧的是,即使人数上多出一倍,依然没有分担他们的负担,“新来的这两人,一个马尔康的,一个红原的,用不上。”电话里他说,“工作基本上还都是由我和D在做。” 二谁来翻译?随之而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但这个追问其实还不够确切,更能说明问题的应该是,它是如何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之所以突出时间维度,不是我在故弄玄虚或是刻意矫情,而在于要有意识地将这个问题嵌入受到中国整体现代化波及的,尽管缓慢,但同样也开始发生在变化了的社会情境的结构中。我们需要由面及点地发现、理解,边疆司法领域从人员组成到审理方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是怎样汇聚到语言并显现出来的。 是因为与当地老百姓语言不通。这当然是事实,首先是藏区的自然条件迫使早已在内地播撒开来的一体化文明难以翻越巍峨峻奇的青藏高原,仍然是自然条件制约了它无法像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发动并最终通过时间达成“书同文”与“语同声”的文化宪制,因此不光是藏语与内地基本通行的语言几乎无任何兼容性可言,而且辽阔的藏区在缺少流动性的情况下各个地方又有自己的一套方言—思维上的惯性很容易将我们快速地引向这个解说。但要注意,存在语言不通这个现象,并不等于这个现象必然是一个问题,更不等于它是一个司法上的问题。因为语言之间鸿沟般的差异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且如果仅仅是与识字率、文盲率有关,那无论如何,今天与10年、0年、解放前相比,藏区的教育普及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可是为什么当我问访约三十年前曾一度生活在藏区的人们时,他们惊呼当时从未感受到语言限制政法工作的开展,甚至怀疑是我不了解情况,那么为什么反倒是在有更多机会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接触,甚至可以通过看电视、听广播、与在学校念书的孩子对话等方式自我矫正发音的今天,语言成为了边疆基层司法的难题? 是的,要留心空间与制度的交错,这主要是边疆基层司法的难题。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浙江、福建、广东也要培训双语法官的?难道温州话、闽南语、广东话就一定比藏语更接近普通话了?为什么同样都是藏区,问题集中发生在天高地远的草原各县政法部门,州府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毗邻成都、都江堰的几个县基层法院就罕有遇到?语言不通对司法正常运作产生的影响是普遍的,但影响的具体后果和解决问题可利用到的资源却是不尽相同的。 要对待语言的问题,却不能本末倒置,观点流露在前文中了,是当语言寄居在边疆司法困境之际才成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那么现代法治在边疆困境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如何发生的呢?理解了这一点,语言问题也就自然地浮出水面。 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线索就是以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展开,如何用统一高效的行政架构、法律政令、意识形态、文化语言将在地域面积极为广袤上生活的亿万民众整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等政治家们的夙兴夜寐,国家的注意力开始不再是帝国时代的占据领土而转移向精耕细作地治理领土上的人口,发展经济,建立一个围绕主权所在地以及政治、商业中心恰当组织的权力均质化国家。 自然历史上“皇权与绅权”分立和有边疆无国界的局面必须改变,国家权力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自然包含法律—或明或暗地从政治金字塔结构的尖端缓缓但坚实地向国家每一寸土地伸进,纵向而言,即向基层下沉,横向而言,则是向边疆推拓。尽管目的一致,但相比内地以农村为代表的基层社会,边疆治理的第一位目标与困难倒还未必是借由送法下乡将暂未充分受到工商文明“格式化”影响的乡土中国以法律的方式进行规训,而是怎样先确保这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土地不独立或者分裂出去,它们无可争辩的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常规条件下谈一切政治、法律的最基本前提与最根本制约。 但这是与生俱来的且永世不变的吗?摆在国家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历史上从来更多属于当地家族、土司、活佛的政治、经济、法律事务,以及更重要的人心,争取到它这方来,如何让边疆生长的人们超越基于现实环境、认定的自己只应当效忠本族群、本地方的直感,升华为心怀祖国、放眼天下的现代公民,如何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干预和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影响下在边疆立定脚跟,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享受中国政府提供的保护而不是其他。这注定将是一场在大约半个中国面积的国土上横空出世的秩序变革。 图:阿坝州卓克基土司官寨 虽说是送法入疆,但送的归根结底其实不是抽象的或者文本的“法”,而是活生生的、办得成事的、属于这个国家法律职业群体的“人”,是靠他们用行动塑造的有现代法律规则意义的实践。之所以人们过去没有觉得语言在藏区等地是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以前的法官就来自本地,他们没有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科班式法学教育和以司法考试为标尺的法官遴选机制,有口才、有威望,抹得平纠纷就可以了,当然前提必须是对国家的忠诚,但这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可能是个问题吗? 当改革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打到了过去闭塞的边疆,曾经无怨无悔的法官也开始讲求更好的物质待遇了,通讯、交通条件的改善使人们追求并且可以追求远离环境苛刻的边疆了,高考制度客观上敦促当地富裕家庭把孩子从小送往内地接受更发达的教育,这些孩子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重点大学里也越来越多地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不仅习得了一口尽管还略带方言的普通话,而且也力图融入、事实上他们中不少人已经融入另一片新天地,也就在此时,他们不自觉地切断了与曾经族群、地域的血肉联系。 图:《马背上的法庭》剧照 当00年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律职业人准入门槛的制度实行以后,在看不出提高了法官办案能力的同时大大加剧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法部门人员的流失,再加上“一刀切”的公务员退休制度使大量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到龄即退休,如果能够像北京、上海等地有削尖了脑袋的后备力量作补充那也不可能成为问题,但是: 第一,原本就留不住人才的物质待遇和艰难困苦的自然条件还想吸引足够的外来人才,不现实; 第二,即使基于其他利益考虑来了,有没有高原反应,会不会朝三暮四,能不能用得上,这些也都是问题,有的基本不是内地会碰到的问题; 第三,因此很大的希望就寄托在外地求了学的少数民族精英能回到家乡,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愿意回到寂寞的藏区吗,家乡有多少人能理解与分享他们在内地五彩缤纷的经历呢? 而且即使回去了,这些从小远离藏区、也自然早早荒疏、遗忘了原本语言的精英法律人真的能担纲,与藏区的—特别是草原上还操持着语音天差地别、但笼统讲也是“藏语”—牧民沟通判案的法官一职吗,就因为通过了司法考试? 因此如今出现了今天像阿坝县政法系统面临的在藏区颇有代表性的吊诡现象:懂得法律专业知识的,忘记了少数民族语言;会说少数民族语言的,则意味着没有接受从后果上看与汉化教育几乎等同的现代教育,他们自然难以通过司法考试,也就无法正式进入国家体制。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现在广阔的藏区派得上用场的干部找不着了。想一想,当藏区的老百姓遇到了纠纷,去据说象征着公平正义的法院,却发现居然无法直接和这些标榜着职业化、专业化的年轻法官沟通时,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还会再来法院吗,还会相信国家当初的允诺吗?甚至,他们还会认同这个国家吗?不要忘记孔子的告诫:“民无信不立。” 尽管讨论的是司法中的问题,但这只是边疆地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的“冰山一角”。“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在市场经济“孔雀东南飞”的今天,为了维持这个不平衡大国的平衡,国家不可能一味坐等时间来调和,而“3·14”事件、“7·5”事件的发生更是迫使国家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快速度输送国家权力,双语政法人才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中以制度的方式凸显了。 三翻译什么?在阿坝县法院与翻译J当面以及后来通过电话与D的访谈中,我留意到一个问题,即翻译工作的重点难点其实不在于诸如案件事实等细节上,而在于设法让当事人理解具有司法程序性意义的法律概念及其相关实践上,例如传票,他们要翻译为用四川话表述为“单单”的语词;又如,回避,则等于要将诉讼法教科书上的定义用通俗的藏语转述一次。但过去并不是这样,不是的原因倒不仅仅在于曾经的司法本身就不需要翻译,而且这里曾经的司法也没有想过把这些“法言法语”视为需要对待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与司法在其协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目的、风格、手段之整体变迁有关,这是双语政法人才出现的另一个理由。 与新中国一直以来向边疆输送国家权力一脉相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通过司法的表达有所不同。0世纪90年代以前藏区的司法几乎完全依附于行政,法院设立的逻辑其实不在于解决纠纷,更不在于确立规则,而是与地方党政机关一道深入边疆,以类似占领据点的形式开始逐步扩展国家在当地的政治、社会影响,纠纷解决只是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必定会面对的环节,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图:入藏干部的代表——孔繁森 但藏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会发生什么纠纷呢?根据阿坝县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执业律师的回忆,整个0世纪80年代,除了三四件工程承揽合同纠纷和极少数的离婚案件,阿坝县几乎找不出民事案件的身影,没有借贷、遗产、知识产权、不动产所有权争议,而刑事案件有的只是传统的偷牛盗马、抢劫、伤害、杀人、强奸这些类型,案情相当清晰简单,因此没有接受多少法学专业训练的人凭借对公平正义的基本把握也能大致够应付个案。对他们而言,采用什么具体形式解决纠纷是次要考虑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化解主要矛盾,维持边疆稳定,至于在当时即使是内地也还若隐若现的法律程序就更上不了他们的心。从外观上这大体是藏区土官“说口嘴”解决本地纠纷的历史延续;他们
|